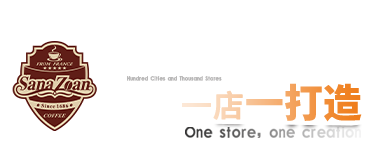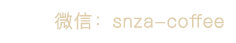四五線城市咖啡館走到岔路口,堂食空間的重要性
作者:塞納左岸小編 發布時間:2023-03-02 16:52:51
行業競爭疊加前兩年的疫情,咖啡圈也在發生巨變。對于要不要擁抱變化、如何擁抱變化,本土品牌走出三類路線:激進轉型派、手藝人、供應商。
第一類以ING coffee、61 coffee為代表。這兩家店都選擇類似Manner的快取店。ING coffee從一開始就下了血本:作為咖啡店最主要的投資,在咖啡機上唐寧選擇了咖啡界的天花板——黑鷹三頭,每臺單價大概在18萬元左右。

這段轉型看起來像從一個極端到了外一個極端。他們8年前開始經營精品咖啡館——拾年,主打私人空間和慢氛圍。
當時唐寧與合伙人剛結束了賠錢的影樓生意,兩人對咖啡所知甚少,還專門跑到云南的咖啡豆工廠偷師,當了半年工人。通過每天晾豆子、烘豆子、磨豆子,反復調整數據,她們把拾年做成馬鞍山最著名的咖啡館之一。
然而疫情這兩年經濟下行,店內入座率一再降低,他們把快消咖啡當成新的出路。但隨著金鷹周邊咖啡店飽和,ING coffee的單日紀錄難以持續。
兜兜轉轉,兩人發現,還是要有堂食。尤其在當前競爭態勢下,賣咖啡依舊需要一個氛圍感。這點與一二線城市明顯不同。
更為現實的是,外賣毛利大概只有30%左右,跟堂食不能比。如果出單量不夠大,容易出現虧損。
唐寧正在考慮,新開門店要帶有少量座位、加入烘焙產品,讓顧客有更多的選擇。“我跟合伙人都是一直往前沖的人,我們想要不停地開店,倒不是說一定要掙多少錢,而是每個店都會給我們帶來一個希望。”
同樣主打外賣的第三鐵道咖啡第二家店,目前仍處于虧損狀態。但陳慶并沒有很擔心這個問題。在他所設計的商業模式中,外賣店的最主要功能不是賺錢,而是提高豆子等原料的使用量,因為只有量上去了,價格才能打下。
不過在咖啡產業鏈當中,陳慶更感興趣的是做咖啡豆供應商、門店運營方案服務商,他們也在朝著這個方向轉型。
愛折騰的江川,準備今年再關停一家業績不太好的門店,最終只保留兩家店。等經濟出現好轉,他準備去南京開一家新店,“既然到哪都是卷,不如去天花板高一點的地方闖一闖。”
至于Drop coffee的林新,比起生意人,他更喜歡稱自己為手藝人。不去考慮商業運作和擴張,在60平方米的空間里烘豆子、賣豆子、賣咖啡,只考慮如何做好一杯咖啡,是陳慶最為向往的事情,“我覺得把一件事做好,自然會有一部分人認可你。”
能讓他煩惱的事不多:咖啡店每天中午才營業,門店與住所僅一門之隔,可以說上班僅需三秒鐘,下班也是三秒鐘。他也不缺客源,顧客大多慕名而來,“有些人說我這里是網紅店,其實我不太愿意聽到這樣的評價。”
林新認為,咖啡本身的好壞才是咖啡店值得被關注的點。大多時候,他在慵懶爵士樂與中古老物件中間悶頭拉花,這份工作帶來的松弛已經超過許多在一二線城市搬磚的年輕人。
當剛入場的撒野coffee還在做養店的第一步——小心翼翼地留住顧客,林新已經不需要再取悅于誰。
想去旅行了,他就在朋友圈發個告示,算是跟老顧客們有個交代,然后把店一關,人就走了。
身心由內而外的自由,大概是三四線咖啡館不斷吸引年輕人加入的一個原因吧。